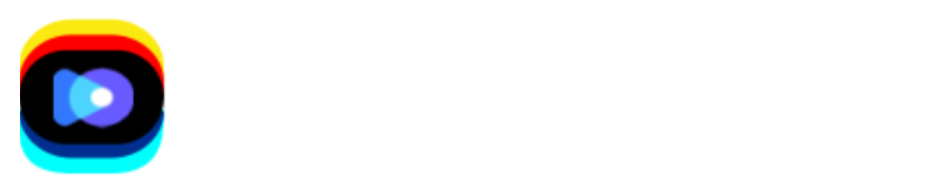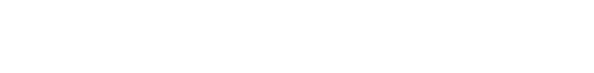西藏题材的电影这些年出来很少,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导致很多创作者不敢触碰这类题材。《藏·爱》是今年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奖影片,通过讲述三个女人深入藏北无人区寻亲的故事来讲述人性光芒和狂暴大自然的搏斗与和解。

影片节奏舒缓,但叙事惊心动魄,故事主角一路曲折坎坷,差点命丧无人区。画面非常精准的捕捉到了藏北无人区的广袤空间和自然的魔幻光影,把人物濒临死亡的心理幻境表现得荡气回肠。
首轮放映结束后,记者采访了张怒涛导演,希望通过他的讲述,了解更多关于电影,关于青年导演的创作理念。

记者:其实我们注意到一般情况下创作者都会选择贴近自己生活、非常熟悉能够驾驭的题材,导演为什么会选择大多数人都觉得陌生和神秘的西藏题材?这其中有什么渊源?
导演:生命的轨迹其实就是由无数个选择串联而呈现出来的,人生因选择而波澜不惊,因选择而步步惊心。我是重度选择困难症,但在必须选择的时候我一般会选最难的选项,因为那些在等待我的未知的世界,那些可能被突破的边界,能够刺激到我去冒险,去为之付出代价。
我喜欢观察人,了解和发现他人的人生,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度,哪个人种,关于人的情感的共性是相通的,我想探究褪去社会赋予的身份、地位、职务,作为人的存在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到底是分还是合。

西藏是我的最难选项,同样,也是故事中人们选择的最难的选项,难到她们要赤裸裸的面对从未遇到过的这个奇幻而狂暴的大自然,他们在这个蛮荒世界如何选择活下去,如何留下她们的生命轨迹?人与人的关系被外界严重压缩,矛盾被激化,褪去所有外在自我觉醒的历程,面对终极死亡问题时该如何选择,我想把这些思考投射到影片中,就必须具备激发这些故事的极端条件,而西藏是最合适的,这是我选择西藏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旅行,带着探寻生命意义的问题四处游荡,西藏地区、尼泊尔、印度这些都是信仰之地,信众由信仰解决此生的诸多苦楚,他们会有许多高于生活的精神体验,这一点和电影十分相似。原住民们在这里诞生了信仰,而我在这里诞生了我的电影,电影是我的信仰。

记者:让你决定拍摄这部影片的契机是什么?从构思到拍摄完成用了多久?
导演:其实一直想做这个故事,但模糊了很久,13年我在藏北旅行的时候猛然想到大自然就是其中一个角色,它狂暴又温柔,变幻莫测,像神秘的爱情,是一个残酷又浪漫的家伙。我们生于自然,又湮没于自然的怀抱,这段关系想通过电影来表述很难,但我还是选择了这种诗意表达。以前没有人做过这种西藏题材,我觉得我应该去尝试一下。
然后我就回到拉萨开始创作,一遍遍的在脑海中架构这部电影,那些画面会一点点生长出来,除了筹备期和各部门负责人的技术讨论,平常我更愿意独自思考。一直到14年底开机,15年第二次开机,又因为部分藏语配音和民族音乐问题多次往返于北京和西藏两地,零零散散的搭着积木,到16年才完成后期,等到正式拿到龙标已经是17年。

记者: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有趣的事?
导演:和大多数低成本影片的困难一样,我们也缺资金。但我觉得把困难和有趣做成一个叠加属性来描述会更有意思。开机前最后一晚我们所有主创坐在一个中巴车里返回拉萨,在荒原土路上和对向行驶的车发生侧撞,我们冲下路肩差点侧翻。大家下车后惊慌失措,但一抬头却看到头顶横跨苍穹的灿烂银河,所有人被美景诱惑就此忘却了车祸带来的烦恼。
缺氧和寒冷是常态,这两个叠加态简直就是噩梦,在无人区的冰湖冻河上,当地流传的是“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头刮到年尾”。狂风是加餐,在这些困难都具备的情况下,我仍然遇到不少有趣的事。

我在等光的间隙爬上无人区的一座小山山顶找景,因为过于疲劳,就地躺下睡着了,迷糊中感到身边有异样,睁眼发现一只硕大的秃鹫飞落在我身边,直勾勾的看着我,我们彼此都被对方吓了一大跳,秃鹰仓皇的飞走了,它把我当成了被献祭的肉身。
电影里有主角和秃鹰对峙的桥段,首映式我给观众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观众问我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体验而创作的桥段。我告诉他,创作在先,而这个桥段在现实中的无人区就真的发生了。我想,那是我无限接近故事主角内心深处的一次体验,秃鹰是带我进入主角内心的一个使者吧。

记者:演员和工作人员如何面对这种特殊情况?你作为导演在拍摄中如何判断和决策?
导演:我们在选择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时候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必须在高海拔地区工作或旅游过,而且没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所有人提前进藏适应,制片人到处化缘搞来一批高原药物和保健品,每天逼着所有人吃药,可以说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扛到无人区最后几天的拍摄时,剧组一半的人都倒下了,剩下的只有我和摄影灯光三个人神采奕奕,越干越勇。现在想想十分后怕,再超期几天可能就要出人命了。
之前和演员有过许多的交流,其实也有很多担忧,但演员从进入无人区开始就全都对了,面对“大自然”这个强大的对手戏演员,演员们无一例外的全都进入了状态,无需多说,也无力多说。
每一场戏在头一天晚上一定会做小品,导演、摄影指导和演员一起参加,除了尽可能在户外保存体能外有些戏份还需要带着日出拍摄,一瞬间的光影变化过去了就又得等一天,所以,等不起。

在影像上前期画面密集,空间逼仄,时间紧凑。后期角色逐渐远离城市,进入荒原时,时间和空间越来越缓慢和停滞,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语言被彻底消失,画面大量留白。这些影像风格前期基本确定,在拍摄前又会再次确认,不夸张的说,现场容不得一丝犹豫。所以,尽管困难重重,但拍摄仍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当然在现有的制片条件下,完成是第一选择,之后只能尽量把遗憾降到最少。
记者:电影中最后主角在濒临死亡的体验,是不是你像表达的对生命的态度?
导演:是的,而且也是整部戏的高潮部分。主角和其他人走散了,进入了广阔的无人区,她遭受了巨大的身心压力,她感到害怕,渴望找到方向,她进入一种临界状态,模糊了现实和幻境的边界,在濒临死亡的痛苦中找到了欢愉的源泉。不夸张的说这也是我对电影创作的感受,我需要这种痛苦作为动力去找到创作的方向,在绝望中挖掘出故事的灵魂。

记者:会在意观众对电影的评价吗?负面评价会打击你继续创作的信心吗?
导演:说不在意很虚伪,其实在观众看到之前就有很多业内业外人都看到了,他们也给了很多评价和意见,我都记下来了。人非草木,看到负面评价我会难受,看到好评就很开心,但也只是一时的情绪,挺一挺平复一下就过去了,再投入工作。
真正可怕的是自己也知道的一些问题,有些是不得已,有些是遗憾,更有智识不足而产生的种种谬误。这样想就肯定很沮丧,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浑浑噩噩一段时间。然后,一个新的想法诞生了,再去创作新的电影,没有时间回想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新故事的刺激和冒险中重新找到快乐。

记者:下一步会选择做什么样的影片?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导演:我希望选题的时候能找到那种在心里猛的撞了一下的感觉,创作永远会尊重内心的冲动,这是让故事强大,观众信服的前提。
现在正在做一部由中国电影基金会扶持的院线电影《奔跑吧紫溪》的后期,聚焦扶贫和可持续性发展,相信不久就会和观众在大银幕上见面。同时还准备启动由我编剧的第三十三届金鸡奖获奖剧本《繁星之城》的拍摄筹备。

另外,受“安全应急宣教进基层”活动小组邀请,参与此次“应急微电影大赛活动”,作为特约导演了解到全国在应急救援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英雄事迹与人物,我希望通过电影镜头忠实的记录和弘扬他们的光荣事迹,为英雄们唱响赞歌,为弘扬正气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安全应急宣教进基层活动组推荐)